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创新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更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015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7 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珠三角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打造粤港澳“9+2”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从发展趋势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随着“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构建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不仅有利于粤港澳深入融合,更有利于带动珠三角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全球生产中心+全球创新中心”,提升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创新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提供重要空间载体[1]。2020年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为金融全方位融入大湾区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展框架下,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创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湾区创新发展城市群尤为重要。因此,研究大湾区城市群创新能力和水平,可为明确大湾区城市群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方向和路径提供参考。
1 文献述评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但随着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入,需从高质量创新结构与水平等角度逐步厘清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方向和路径。在大湾区创新发展研究文献中,创新理论提供了研究基础。其中,Freeman[2]提出技术不只是企业家的专利;Furubotn[3]提出制度创新决定社会演进方式。另外,创新生态系统是比较新颖的视角。其中,辜胜阻等[4]认为应协同推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刘雪芹等[5]认为,要从基础体系、运行支撑体系、演化引导体系3个方面推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Lundvall[6]认为创新系统的核心是互动学习。从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角度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其中,Soleolle[7]认为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具有显著推动作用;Bergman[8]从创新网络化视角进行研究;洪银兴[9]认为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还要有激励创新的环境;许培源等[10]提出应着力强化深圳的创新网络中心地位;毛艳华[11]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要消除要素跨境流通障碍,强化湾区跨境政策协调,形成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蹇令香等[12]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处于低度协同发展状态,协同化进程较慢;钟韵等[13]认为应提高区域内制度性整合效率,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武汉大学资本赋能大湾区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组[14]认为,让股权投资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创新高地建设,应资本来源,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杨英[15]认为,粤港澳三地应该相互对接、实现双向融合;魏丽华等[16]认为,应优化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阳国亮等[17]认为,珠三角经济圈向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分工体系重构;苏振东[18]认为“CEPA预实验”对当前广东自贸区建设有一定借鉴作用;向晓梅等[19]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全面融合应以协同研发和市场共同开拓为重点;梁经伟[20]认为湾区应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优化市场结构、鼓励风险投资企业与创新企业融合,进而提升湾区活力和竞争力;宋洋等[21]认为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应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Taylor[22]认为复杂网络系统节点与其它节点间的相关性、流动性和密集性决定了城市地位变化。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和行业发展视角的研究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Gunasekaran[23]关注了持续发展及其竞争力;杨明海等[24]研究发现,区域间差距是科技创新能力呈现空间异质性的主要根源;霍国庆等[26]构建了中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模型;张峰等(2017)认为,应该重点推动生产要素跨界融合与产业均衡发展;李燕[26]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地理邻近、技术邻近和制度邻近3个维度上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曹霞等(2015)认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资助、教育受重视程度、产权保护意识及信息化水平均是促进研发创新效率提升的有利因素;谷亚光等[27]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刘云等[28]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要素-制度-功能-阶段”四维分析模型;苏屹等(2016)提出应从增强创新效果、优化创新配置、提升创新潜力3个方面促进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鲁志国等[29]提出国内城市应注重发挥区域特色和强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 桂黄宝[30]通过构建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上述文献主要从多主体联动、发展模式、协同创新、跨区域要素对接、知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量化研究,但通过构建协同创新发展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水平的量化研究较少,本文重点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2 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主线与方法
2.1 研究主线
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进行研究,要考虑创新形成和发展的各个环节。首先,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出发,以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方面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的研究主线,构建相应评价指标;其次,根据各城市指标水平优劣情况,提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思路。各指标结构具体如下:
(1)创新环境水平。高质量创新发展不仅要依托现有发展基础,掌握当前创新发展水平,而且要在此基础上优化创新环境水平。首先,高质量创新发展环境水平应结合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衡量,而人均GDP就体现了创新环境物质基础水平,GDP水平越高,创新环境物质基础水平也就越高;其次,高质量创新发展主要依靠人才,而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人口数量的比重直接体现了高质量创新发展人才储备水平,其占比越高,反映创新环境水平也就越高;再次,每百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占人口数量的比重反映了当前直接从事创新工作人员的相对规模水平,其占比越高,创新环境水平也越高。
(2)创新投入水平。创新投入水平直接影响创新产出水平,是创新发展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首先,创新投入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资金规模上,R&D占GDP的比重直接体现了区域创新发展中R&D投入的相对规模水平,其占比越高,创新投入水平也越高;其次,公共财政对创新投入资金规模也非常重要,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比重直接体现了公共财政对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其占比越高,创新投入水平也越高;再次,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反映了企业创新投入资金规模和水平,体现了创新主体创新投入意愿和水平。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用创新人力资源数量衡量,人才投入水平越高,创新投入水平也越高。
(3)创新产出水平。创新产出水平是指在创新环境中通过创新投入作用而产生的创新成果,是衡量创新成效水平的重要指标。首先,创新的主要产出就是新产品产出数量,而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体现了市场化导向创新成果水平,其金额越大,表明创新产出水平越高;其次,专利授权数量是国际通用的创新成果水平衡量指标,每万人口专利授权量直接体现了创新成果水平,其数量越多,表明创新产出水平越高;再次,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反映了市场化导向下技术创新交易活跃程度,而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则直接体现了市场化导向下的科技创新成果水平,其金额越大,表明创新产出水平越高。
2.2 指标体系
本文通过对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的分析,同时考虑到总目标、3个子目标和各个具体指标的层级、内涵功效和数据可得性,经过细化,构建出包括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10个指标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总目标子目标指标指标衡量方式功效创新环境人均GDP人口数量/GDP +高等教育人口占比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口数量+每百人中的工业企业R&D人员(工业企业R&D人员/人口数量)*100+创新投入R&D占GDP的比重R&D支出//GDP +高质量创新发展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占比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支出 +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R&D经费内部支出/人口数量+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万人年)+创新产出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人口数量+每万人口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人口数量(万人)+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人口数量(万人)+
本文对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10个指标进行阐述。在创新环境方面,从经济发展人均水平、人才储备规模、现有研究人员数量3个维度考察,这3个指标描述了创新环境水平,分别用人均GDP、人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和每百人中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3个指标衡量;在创新投入方面,从研究开发支出水平、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水平和R&D经费内部支出水平3个维度考察,具体以R&D投入占GDP的比重、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3个指标反映创新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从新产品销售金额、专利授权数量和技术合同交易金额3个维度考察,具体以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每万人口专利授权数量和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3个指标衡量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表1给出了各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
2.3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设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3个维度,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水平和综合水平进行分析。首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赋予各指标一定的权重值,并适当微调,在处理过程中考虑各指标相应功效,通过加权计算,得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其次,分别按各子目标指标评分和综合评分降序排列,确保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矩阵和数据标准化处理。首先,确定m个评价对象的n个评价指标数据矩阵,Xij(i=1,2,…,m;j=1,2,…,n),对各指标对应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原始数据矩阵为:
 (1)
(1)
其次,运用极差法对各指标Xij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不同指标在数量级方面的一致性。
 (2)
(2)
其中,i表示各城市,j表示各指标,Xij、Yij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发展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后的指标水平值。max(Xij)、min(Xij)分别表示Xij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计算各指标Yij的信息熵Ej。
 (3)
(3)
(3)计算各指标Yij的权重Wi。
 (4)
(4)
(4)计算得出指标的加权矩阵S。
S=(sij)n×m 。其中,sij =Wj×Yij(5)
(5)根据功效和数据可读性对加权矩阵S进行调整。从表1中可见,3个子目标10个指标的功效均为“+”。对S进行功效处理得出S',为方便sij 数据读取,对第四步中的sij扩大倍数后得出s'ij,分别得到各指标得分。在综合得分方面,将各城市的 加和后得出综合得分。
加和后得出综合得分。
本文各项数据分别来源于2018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广东省9个大湾区城市2018年统计年鉴,各项含有币值金额的项目均以人民币为单位。香港数据来源于《2018年香港统计年鉴》《2018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香港创新促进局2018—2019年报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2018年统计数据》。其中,各项指标中含有港币的金额均以2018年12月31日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1∶0.877 7换算为人民币值。澳门数据来源于《2018年澳门统计年鉴》《澳门2018年4季度经济发展报告》和澳门统计调查局2018年时间序列资料库,其中各项指标中含有澳门元的金额均以2018年12月31日澳门元对人民币中间价1∶0.779 87换算成人民币值。
3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实证研究
3.1 大湾区创新发展各子目标水平
通过构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计算得出2018年大湾区“9+2”区域高质量创新发展3个子目标10个指标的得分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各子目标水平

城市创新环境人均GDP(万元)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工业企业R&D人员(人/百人)创新投入R&D经费占GDP的比重%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万元/年)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万人年)创新产出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专利授权量(百件/万人)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万元/人)广州2.696 0.027 0.287 1.449 3.912 0.108 3.886 1.953 0.331 0.196 深圳3.268 0.003 0.994 2.644 7.764 0.445 6.216 5.551 0.592 0.182 珠海2.709 0.027 0.729 1.741 4.763 0.263 1.289 4.499 0.497 0.092 佛山2.209 0.006 0.528 1.410 4.068 0.178 3.632 3.067 0.035 0.004 惠州1.493 0.003 0.465 1.267 2.438 0.111 2.251 3.546 0.167 0.006 东莞1.734 0.005 0.597 1.570 3.079 0.158 4.851 6.441 0.432 0.009 中山1.929 0.006 0.495 0.925 5.614 0.107 1.414 2.050 0.567 0.003 江门1.109 0.004 0.293 1.190 2.103 0.076 1.203 1.446 0.147 0.006 肇庆0.932 0.009 0.135 0.567 1.324 0.032 0.475 0.663 0.052 0.000 2 香港5.891 0.015 0.179 0.474 0.132 0.078 0.737 0.192 0.077 0.088 澳门9.049 0.019 0.313 0.000 2 0.001 0.021 0.180 0.079 0.074 0.033 均值3.002 0.011 0.456 1.204 3.200 0.143 2.376 2.681 0.270 0.056
注:①数据均根据功效调整;②本文纳入研究的9+2区域共11个城市,其中广东省9个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2个特别行政区为香港和澳门
(1)人均GDP。人均GDP水平得分最高的澳门(9. 049)为得分最低肇庆(0.932)的9.7倍,表明大湾区间人口生活水平差异非常明显,不同城市人口生活水平各异。具体来看,人均GDP水平得分高于2.500的城市有澳门、香港、深圳、珠海和广州5个城市,占比为45.5%,表明这些城市人均GDP水平较高,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创新发展物质基础较好。人均GDP水平得分低于2.500的城市有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和肇庆6个城市,占比为54.5%,表明这些城市人均GDP水平较低、创新发展物质基础薄弱。据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均GDP仍然存在不平衡现象,尤其是肇庆、江门、惠州等城市与均值差距较大。这一方面说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为各大湾区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空间。
(2)高等教育人口占比。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水平得分较高的城市为珠海(0.027)、广州(0.027)、澳门(0.019)和香港(0.015),得分较低的城市为深圳(0.003)、惠州(0.003)和江门(0.004)。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8倍,表明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空间差异较大。综观各城市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水平得分发现,广州、珠海、澳门、香港4个城市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水平得分等于或高于0.015,创新技术人才储备水平领先,凸显了后续发展的有利条件。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水平得分高于均值0.011的城市有4个,占比为36.4%;教育人口占比水平得分低于均值0.011的城市有7个,占比为63.6%,表明半数以上城市高等教育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得分最高的深圳(0.994)是最低肇庆(0.135)的7.4倍,表明工业企业R&D人员投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间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也各异。具体来看,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得分高于0.700的城市只有深圳(0.994)和珠海(0.725),占比仅为18.2%,表明深圳和珠海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较高、基础条件较好,显现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高于均值0.456的城市有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惠州,占比为54.5%,表明这些城市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相对领先,基础较好;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得分低于均值0.456的城市有澳门、江门、广州、香港、肇庆,占比为45.5%,表明这些城市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水平相对较低,说明大湾区部分城市创新人员投入与创新环境协调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4)R&D经费占GDP的比重。R&D经费占GDP比重得分最高的城市是深圳(2.644),得分最低的城市是澳门(0.000 2),前者是后者的13 220倍,表明R&D经费占GDP比重水平空间差异十分明显,经济结构与发展导向性差异较大。综观各城市R&D经费占GDP比重水平得分发现,深圳、珠海、东莞R&D经费占GDP比重水平得分高于1.500,它们是大湾区R&D经费占比水平非常领先的城市,凸显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特点。R&D经费占GDP比重水平得分高于均值1.204的城市有6个,占比为54.5%,其中深圳、珠海、东莞、广州、佛山、惠州得分分别为2.644、1.741、1.570、1.449、1.410、1.267,均高于1.204,属于R&D经费支出水平较为领先的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导向性十分突出;R&D经费占GDP比重水平得分低于均值1.204的城市有5个,占比为45.5%。据此可见,近半城市仍有较大的创新投入提升空间。
(5)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水平最高的5个城市依次为深圳(7.764)、中山(5.614)、珠海(4.763)、佛山(4.068)和广州(3.912),表明这些城市十分重视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创新发展,将创新发展支出列为城市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体现了高质量创新发展导向下财政支出管理水平。与之相反,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得分最低的3个城市为澳门(0.001)、香港(0.132)和肇庆(1.324),表明这些城市不太重视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创新发展,财政支出高质量创新发展导向性不明。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水平高于均值3.200的城市有5个,占比为45.5%;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得分低于均值3.200的城市有6个,占比为54.5%。而且,粤港澳差异十分明显,广东省内9个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水平得分明显高于香港和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粤区城市与特别行政区城市公共财政支持创新发展的导向性差异十分明显。
(6)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水平得分最高的4个城市为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得分分别为0.445、0.263、0.178、0.158,这些城市十分重视高质量创新发展,内部R&D经费投入力度较大,较好地体现了创新发展理念。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水平得分较低的城市依次是澳门、肇庆、江门、香港,得分分别为0.021、0.032、0.076、0.078,这些城市企业内部研发投入水平较低,高质量创新发展投入明显不足。因此,应根据资金和资源条件,加大协同创新投入力度,逐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
(7)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水平得分最高的城市为深圳(6.216),得分最低的为澳门(0.180),前者与后者相差6.036,其它城市得分水平差异较为明显。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水平得分高于均值2.376的城市有4个,占比为36.4%,前4个城市为深圳(6.216)、东莞(4.851)、广州(3.886)和佛山(3.632);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水平得分低于均值2.376的城市有7个,占比为63.6%,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后6位的城市为中山(1.414)、珠海(1.289)、江门(1.203)、香港(0.737)、肇庆(0.475)、澳门(0.180)。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水平得分最高的深圳优势十分明显,大大高于均值2.376,其R&D人员投入水平较高,R&D人员集聚性投入水平较高,引领高质量创新发展导向明确。
(8)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水平得分最高的城市是东莞,达到6.441;深圳和珠海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得分分别为5.551和4.499。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水平得分高于均值2.681的城市有5个,占比为45.5%;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水平得分低于均值2.681的城市有6个,占比为54.5%,得分排名后3位的城市为肇庆(0.663)、香港(0.192)和澳门(0.079)。得分最高的东莞在新产品销售收入方面具有较为领先的优势,突出了其工业制造核心基地地位。
(9)专利授权量。人均专利授权量水平得分最高的城市是深圳(0.592),第二到第五位依次为中山(0.567)、珠海(0.497)、 东莞(0.432)、广州(0.331);专利授权量水平得分高于均值0.270的城市有5个,占比为45.5%;专利授权量水平得分最低的4个城市分别为香港(0.077)、澳门(0.074)、肇庆(0.052)和佛山(0.035)。深圳得分仍然最高,体现了最具活力的创新因素在其高质量创新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并发挥引领作用。
(10)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水平得分前3的城市依次是广州(0.196)、 深圳(0.182)和珠海(0.092);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水平得分高于均值0.056的城市有4个,占比36.4%;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水平得分最低的5个城市分别为江门(0.006)、惠州(0.006)、佛山(0.004)、中山(0.003)、肇庆(0.0002)。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水平得分普遍偏低,城市间差异较大。总体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市场高质量创新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3.2 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
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得分情况看,各城市综合水平得分整体都不高。为方便比较和评价,本文以各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结果加上基础分70分,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最终得分,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介于74.189~97.660之间;其中,综合得分水平最高的城市为深圳(97.660),综合得分水平最低的城市是肇庆(74.189)。从统计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样本均值 样本标准差Ŝ=6.436,不同城市在高质量创新发展中差异显著。根据各城市得分样本均值A与样本标准差Ŝ的统计性质,为进一步对各城市得分水平进行研究,将11个城市划分为得分高于86.616的引领型
样本标准差Ŝ=6.436,不同城市在高质量创新发展中差异显著。根据各城市得分样本均值A与样本标准差Ŝ的统计性质,为进一步对各城市得分水平进行研究,将11个城市划分为得分高于86.616的引领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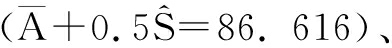 得分介于86.616~80.181之间的中等型
得分介于86.616~80.181之间的中等型 至
至 和得分低于80.181的落后型
和得分低于80.181的落后型 种类型。
种类型。
由统计分析可知,引领型城市有2个(深圳和东莞),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总数的18.2%,其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分别是97.660和88.878,均高于86.616,表明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十分突出,特别是在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R&D经费内部人均支出和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3项得分上具有领先优势,尤其重视创新资金投入和创新人员投入,在创新人员数量和专利授权方面表现较好,综合表现优异。其中,深圳的引领作用十分突出,是唯一一个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超过90分的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最高的城市,充分体现了深圳引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绝对优势。中等型城市有5个,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总数的45.5%,分别为珠海、佛山、广州、中山和惠州,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分别为86.609、85.137、84.845、83.111和81.747,介于80.181~86.616之间,反映出创新发展环境条件中等、创新投入和产出稍显不足、效果不明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偏低型城市有4个,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总数的36.3%,分别是澳门、香港、江门和肇庆,其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依次为79.769、77.862、77.576和74.189,得分均低于80.181。由此可见,这些城市受资源环境基础、经济结构和创新投入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其高质量创新发展投入力度不足,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得分偏低,但可以与引领型城市和中等型城市形成优势互补的创新发展格局,从而为提升大湾区综合创新能力和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水平3个子目标的10个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高质量创新发展研究,根据大湾区11个城市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得出如下结论:
(1)从3个子目标10个指标得分看,大湾区11个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子目标水平各异。具体而言,澳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人均GDP水平较高,人们生活相对富裕,经济发展物质基础较好,具备较好的创新发展条件,金融和资本市场发达;珠海、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城市高等教育人才储备水平较高,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人才支持;深圳、珠海、东莞和佛山等城市已投入的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较多,具备良好的科研人员基础和条件,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研发人力资本;深圳、珠海和东莞等城市R&D经费占GDP的比重较高,R&D投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投入占比较多,R&D资金投入较大,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研发资金;深圳、中山、珠海、佛山和广州等城市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水平较高,政府创新发展投入意愿较强,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具备较好的政府公共财政支持条件,能够吸引较多创新资源,也是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基地,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核心和中心基地支撑作用;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等城市R&D经费内部支出人均水平较高,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较强,研发人均投入水平较高,企业研发氛围浓厚,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较好的创新发展氛围;深圳、东莞、广州和佛山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水平较高,企业研发投入专业人员较多,具有非常大的创新人才集聚优势,能够为大湾区创新协同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研发人员和产业导向支撑;东莞、深圳、珠海、惠州和佛山等城市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水平较高,作为创新发展主要成果的新产品市场销售金额较大,创新成果十分显著,高质量创新发展优异成果较多,是大湾区创新成果体现最为集中的城市,在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方面发展水平均较高,作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核心城市,可持续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创新发展;深圳、中山、珠海、东莞和广州人均专利授权量水平较高,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创新动力和较为雄厚的技术基础;广州、深圳、珠海和香港人均技术市场交易水平较高,说明其技术供给和需求强烈,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转化动力,能够为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技术储备和市场化交易条件。
(2)从综合水平看,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平均得分为83.398,根据11个城市得分均值和方差统计对各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其中引领型城市有2个,占18.2%;中等型城市有5个,占45.5%;偏低型城市有4个,占36.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整体上呈现出“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大湾区城市群创新主体聚集性高、产业体系完备、金融发达,创新环境优、开放程度高、优势互补性较强,具备实现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打造世界一流创新湾区的条件。
4.2 政策建议
为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全面协同提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强化创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调发展。当前,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仅为83.398,仅有深圳得分高于95分,创新发展优势非常明显,其它多数城市处于创新发展中等水平,偏低型城市数量占比高达36.3%。人均GDP、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4个因素对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影响较大,即环境因素1个、投入因素2个、产出因素1个。因此,为持续有效提升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最关键的就是加大创新力度,促进大湾区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大创新财政支持力度及创新人员投入;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升新产品市场规模和水平。根据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3个子目标的10个指标,结合各城市实际和各自优势,统筹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互动,逐步凸显各城市优势,协同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
(2)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各城市各子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持续推进高质量创新发展各个子目标水平全面提升。本文研究发现,深圳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最高,但在人均高等教育数量方面略显不足;香港和澳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才储备条件较好、金融市场发达、资本国际化水平高、贸易便利,但创新意愿、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均不高,各城市普遍都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大湾区各城市应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形成有效互补,制定有针对性的提升策略。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广东省9个湾区城市的经济发展结构,同时也要关注香港和澳门资金、资本、经贸便利化等优势,使其与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形成互补、互动和协同发展,促进创新资金投入、人力投入和新产品研发水平提升,持续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各子目标水平协同提升。
(3)抓住重点、有效突破,结合大湾区规划纲要和金融支持意见,实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协同优化策略,通过协同发展,形成创新和资本的有效结合,逐步缩小城市间差距,不断提升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子目标和综合得分各异,且城市差异十分显著。深圳和东莞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领先地位相对显著,珠海、佛山和广州创新发展水平较高,广州在人才储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香港和澳门具有非常明显的国际化资金、资本、贸易和人才优势,但大湾区只有2个城市属于引领型,仍有5个城市属于中等型,4个城市属于偏低型,这种分布对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且各城市优势互补水平和效果亟待提升。因此,应抓紧制定各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政策,充分利用深圳、东莞、珠海、佛山和广州的创新发展优势以及制造业发达的良好基础,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在资金资本充足、贸易便利化、人才国际化等方面的优势,形成良性发展互动机制,同时辐射带动其它4个城市创新协同发展;通过持续推进各城市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创新资金和资本投入,有效运用创新成果,深化证券、银行、保险、外汇等制度创新,让科技真正赋能产业发展,逐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各城市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水平。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①虽然采用量化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和协同化分析,但在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方面指标比较单一,未来可对大湾区创新要素构成情况进行完善,不断丰富指标体系,从而凸显国家战略发展层面的引领性作用;②在统计数据来源方面,由于两种制度中3个不同区域根据各自管理需要和实际发展所确定的统计资料和关注重点不同,因此结论存在差异。未来可在区域可比性方面进行细化和深入研究,找出大湾区创新协同发展的互补点;③从协同发展角度看,还需借鉴世界著名湾区创新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从全球视角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创新协同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Z].2019.
[2] FREEMAN C.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97.
[3] FURUBOTN E G,RICHTER R.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
[4] 辜胜阻,曹冬梅,杨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J].中国软科学,2018,328(4):1-9.
[5] 刘雪芹,张贵.创新生态系统:创新驱动的本质探源与范式转换[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33(20):1-6.
[6] LUNDVALL B A.Product innovation and user-producer innovation[M].Aalborg University,1985.
[7] SOLÉ-OLLÉ A,VILADECANS-MARSAL E.Central cities as engines of metropolitan area growth[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4 (2).
[8] BERGMAN E M.Embedding network analysis in spatial studies of innovation[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9,43(3):559-565.
[9] 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169(5):5-11.
[10] 许培源,吴贵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兼论深圳科技创新中心地位[J].中国软科学,2019,341(5):68-79.
[11] 毛艳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南方经济,2018,351(12):129-139.
[12] 蹇令香,李辰曦,曹卓久.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研究[J].管理现代化,2020,40(1):16-20.
[13] 钟韵,胡晓华.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J].经济学家,2017,228(12):50-57.
[14] 武汉大学资本赋能大湾区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组.让资本赋能大湾区全球创新高地建设[J].南方经济,2019,357(6):1-9.
[15] 杨英.新时期粤港澳经济更紧密合作的基本趋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2(4):97-103.
[16] 魏丽华.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J].经济纵横,2018,386(1):45-54.
[17] 阳国亮,欧阳慧,程皓.区域合作空间维度的最优圈层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分工体系的纵深拓展[J].经济问题探索,2018,430(5):80-89.
[18] 苏振东,赵文涛.CEPA:粤港贸易投资自由化“预实验”效应研究——兼论构建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实证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2016,271(9):18-134.
[19] 向晓梅,杨娟.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模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32(2):17-20.
[20] 梁经伟,毛艳华,江鸿泽.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8,430(5):90-99.
[21] 宋洋,王志刚.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路径研究——以新常态下2010—2015数据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6,34(5) :61-64.
[22] TAYLOR P J.Regionality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4,56(181):361-372.
[23] GUNASEKARAN A,SUBRAMANIAN N,YUSUF Y.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for inclusive manufacturing:twenty-first-century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2018,31(6) :490-493.
[24] 杨明海,张红霞,孙亚男,等.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4):3-19.
[25] 霍国庆,杨阳,张古鹏.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模型的构建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38(6):77-93.
[26] 李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R&D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多维邻近性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9,346(11):138-144.
[27] 谷亚光,谷牧青. 论“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创新、理论内涵与贯彻重点[J].经济研究,2016,439(3):1-6.
[28] 刘云,谭龙,李正风,等.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及测度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36(9):1324-1339.
[29] 鲁志国,潘凤,闫振坤.全球湾区经济比较与综合评价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1):112-116.
[30] 桂黄宝.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2014,34(6):100-107.
(责任编辑:王敬敏)

![]()

 (1)
(1) (2)
(2)
